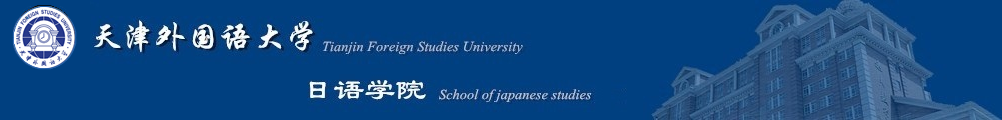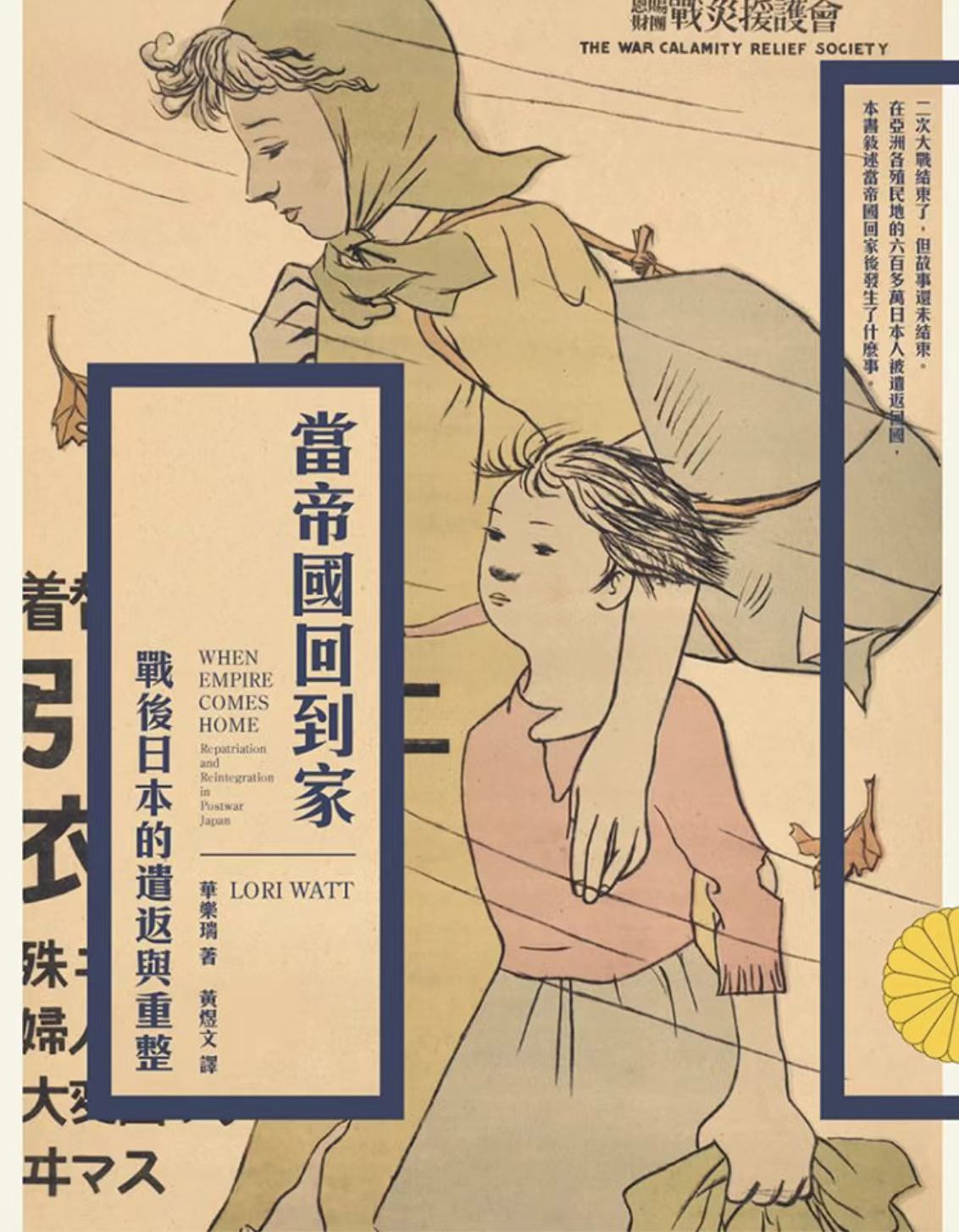
《当帝国回到家:战后日本的遣返与重整》
华乐瑞著,黄煜文译,
远足文化出版社,2018年1月
蔺静
天津外国语大学日语学院
【导读】在《当帝国回到家:战后日本的遣返与重整》中,华乐瑞以制度史视角揭示了日本帝国遗民如何在战后“同质国民”的结构中被建构为难以容纳的“内部他者”。而从制度之外的个体自觉出发,对于法西斯体制的反省应以责任承担为起点,经由持续的日常行动,迈向公共参与,最终完成对历史的回应与“精神返迁”。【关键词】法西斯体制 双重暴力 精神返迁
一、“归来”的转译:从历史责任到行政治理的结构性变形
潮湿的码头、刺鼻的药水味、蜿蜒排队的身影,构成了战后日本国家记忆中“归来”叙事的典型场景。从1945年秋到1946年底,以美国为主的盟军(以下简称“驻日盟军”)以“去军事化”与战后秩序重建为目标,主导了日本帝国解体所引发的大规模人口迁移,不仅在短时间内将日本人从殖民地迅速撤回,也将“前殖民地人民”送离日本。这场被称为“返迁”(日文为“引揚”)的行动,重绘了战后国家边界,通过“民族分离”取代了帝国时期的混居结构,奠定了战后日本同质性社会的制度基础。然而,正如美国研究日本近代史学者华乐瑞(Lori Watt)在其著作《当帝国回到家:战后日本的遣返与重整》(台北:远足文化,2018,以下简称《当帝国回到家》)中所指出的:“当战败的消息传来,殖民地日本人与本土日本人所处环境的差异立时显见。殖民地与本土之间的紧张关系,一部分表现在1945年时个人是身处于本土之内还是之外。”[1]这一断裂性的瞬间,既揭示了殖民地与本土日本人在战时经验上的结构差异,也为本书确立了贯穿始终的分析视角,构成理解全书问题意识的重要切口。
京都府北部的舞鹤港,作为主要接收港口之一,成为战后日本治理逻辑最集中、最具象征性的实践场域。返迁者必须依次完成登记、接受DDT消毒、身份确认、衣物处理与预防接种等流程,方能重新跨入“祖国”的制度门槛。返迁者不再是帝国的臣民,而是在战后国家体制中被重新命名、分类与管理的行政对象。通过这一深具政治意图的重编,国家得以悄然将帝国的崩塌转译为一个行政难题。
与此同时,返迁者个体的叙述方式与这一治理逻辑紧密关联。大量口述与回忆材料通过强调苦难,构建无辜的生存经验,强化了归来者的“无害”形象,帮助其争取社会同情与政策支持。这些讲述不仅富有“情感力量”,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策略。媒体在其中亦扮演了关键角色:配合国家治理意图的新闻报道、杂志摄影和纪录片等频繁展示返迁者接受检疫与身份核查的画面,塑造了“归来”的图像,并将其不断复制,固化为国家重建秩序的一部分。[2]在视觉单一化的压制下,来自“满洲”的农垦者、上海的企业职员、朝鲜的家庭主妇等,其经历的多样性被抹平,最终被统一标记为“返迁者”。舞鹤港因此不仅是历史的见证地,也是身份的生成地。
返迁者之所以能够迅速获得日本社会的默认,正是由于制度、媒体与个体讲述三方机制的协同作用。在盟军主导、日本行政体系配合之下,帝国的解体被迅速转化为人口划界与行政管理;媒体通过统一图像重塑“归来”的社会想象;个体则以苦难为通行证,回避了自身在帝国体系中曾扮演的角色。三者共同构成了一个深刻的悖论:帝国疆界虽已崩解,分类秩序却依旧存在;军国主义语言退场,身份治理却被不断加码;原本应进入公共讨论的“反省”与“责任”,却被迅速转化为“风险”与“救济”的技术程序。当历史被简化为技术事件时,我们应警觉:这种去政治化的叙事逻辑,正是法西斯主义内向暴力延续的形式之一,也是理解战后日本如何重塑自我、规避战争责任的关键入口。
二、“苦难即无辜?”:返迁叙事中的污名机制与责任空缺
在《当帝国回到家》中,华乐瑞聚焦于两个典型的返迁群体:1946年夏自“满洲国”归来的女性与1949年自西伯利亚归国的男性。前者一踏上码头,便被社会舆论与国家制度以“民族纯洁”“优生焦虑”的标准检视;后者因被视为“红色返迁者”而卷入冷战初期的政治审查与就业排斥中。这两类看似分离的污名路径,却共同构成了战后日本对“例外者”的内部治理机制。
对“满洲国”的归国女性而言,战后日本社会首先关注的往往不是她们“殖民经历中的困境”,而是她们是否依然“纯洁”。女性在归国后,普遍面临婚姻市场的排斥、职场的不信任以及日常生活中的隐性歧视。在小说《紫丁香盛开的五月到来》中,一句台词“我的血是纯洁的!”[3]揭示了战后日本如何通过家庭化语境,将殖民责任转化为个体羞耻,让女性承担其中的道德代价。女性则通过“逃难”“饥饿”“照顾老幼”等“清白场景”重构自我形象,形成一种“适应性叙述策略”。与女性的“身体污名”相对,西伯利亚归国男性则被贴上“思想污染”的标签。自1949年起,返国士兵迅速被归为“红色返迁者”,并因“政治不稳定”“思想不纯”“难以服从”而被排除于主流劳动市场。男性则通过强调高强度的体力劳动、长期疾病与求生技巧,试图证明自己“未被改造”。
在这一社会语境下,谁能更早提供“无害证据”,谁就更有可能在资源匮乏的战后日本获得安置、就业和婚配的机会。通过污名化“例外者”,日本社会迅速构建起以“勤劳、服从、不涉政治”为核心的国民规范,并将帝国遗产中的暴力与责任转嫁给那些“曾在外”的人。个体一旦被标记为“例外者”,其作为战争见证者的可信度便被削弱。这种去主体化的过程迫使个体必须不断诉诸“清白”,进而难以正视自己的加害角色:当我必须证明自己“无辜”时,我又如何能承认自己曾是暴力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盟军占领时期延续下来的法律与行政话语体系,也在不断强化这一逻辑。1957年与1967年两次补偿立法的修订,表面上看似肯定返迁者“为国牺牲”,但实质上是对帝国暴力经验的再国家化处理。原本应当促成反思的殖民历史,在“纪念”的名义下被削弱其锋芒,使得返迁者更难以提出自我追责的主张,也阻滞了帝国责任在公共领域中的有效讨论。
战后大众文化在这一过程中充当了“扩音器”。华乐瑞分析了战后文艺作品中返迁形象的表达,其中“怨”与“羞”是交织的核心主题。例如,电影《仪式》片头主人公的感叹:“我们平安逃离了俄国人、满洲人与韩国人的掌控。最终,却落入日本人的手里。”[4]这段话揭穿了国家“回归叙事”的虚假表象,直指战后社会对归来者的排斥。《流浪的星星还活着》等战后流行作品,以歌颂苦难、等待与归乡为名,却往往将复杂的历史经验简化为可消费的“苦情剧场”[5],以抒情感伤掩盖对帝国殖民的反思,在强化“我们是受害者”的同时,进一步削弱了加害者身份的可见度。
制度、媒体与个体讲述的共谋,使“苦难等同于无辜”成为返迁叙事的核心逻辑,塑造出一种既唤起同情又规避反思的“返迁哀史”[6]叙事模式。然而,个体是否能够突破“例外者”的标签,转而成为战争历史的能动叙述者;他们是否能从个人经验出发,开启对帝国与自我的双重反思:这正是《当帝国回到家》提供的理论空间中最具延展性与现实意义的部分。华乐瑞细致揭示了帝国以何种形式“回到家”,却尚未触及一个更为关键的追问:帝国,是否真的回过家,又该如何回家。
三、穿越制度的缝隙:精神返迁的可能与行动
《当帝国回到家》较少描写制度缝隙中那些无人要求却仍有人主动承担的个人行动。事实上,正是在这些缝隙之中,一些个体选择了逆流而行:有人选择留在曾经的殖民地社会,以日常劳动回应殖民历史的遗留问题;有人则在日本社会内部,坚持将战争与帝国重新拉回公共视野。这些行动者的存在构成了制度之外难以归类的个体,走出了一条超越“风险与救济”框架的路径。
如果将战后归国视为一种“道德旅程”,那么战后在中国生活数十年的妇产科医生山口秋子(在中国名为刘岩)与日本社会学家小熊英二的父亲小熊谦二,分别踏上了两条看似不同却殊途同归的“回家之路”。他们并不把自己视为故乡的负担,而是意识到自身既是帝国体制的承受者,也应成为回应历史的承担者。
刘岩的生命轨迹在日本战败之日被彻底改写。那天,她与丈夫因羞耻与绝望企图双双自尽——她被中国邻人所救,脖颈上留下伤疤,此后常年以丝巾掩饰。她选择留在中国,作为一名产科大夫,50年间在吉林省舒兰的丰广矿区接生了一万余名婴儿。她以点点滴滴的日常劳作,逐渐缓解了周围人对日本人抱持的戒心与敌意,将脖颈上的疤痕和“小日本”的外号转化为一双“可信任的手”。她没有在日本内部争取“受害者”的位置,而是选择在他者的出生与成长中,长期承担那份无法抹去的历史责任。
直到20世纪90年代,刘岩才踏上归国之路,但她的“回家”早已超出地理或法律的意义,而是在日常生活中悄然完成。她曾说:“战争是让人成为非人的东西。”接生,便是她的“救赎之道”。她以日复一日、踏实温柔的劳动,让自己重新成为“人”,不再仅仅是历史标签下的个体,更是一个能够照料他人的主体。对她而言,“回家”是在曾经造成伤害的地方,重新成为一个能够赢回他者信任的人。
与此相映照的是小熊谦二的另一条路径。他从西伯利亚劳改营归国后,在身体病痛与经济困顿中过着普通市民的生活。他不热衷政治,但会抽空读士兵回忆录、索尔仁尼琴,加入国际特赦组织。退休后,他飞去波兰看奥斯威辛;在投票上,他厌恶含糊其词的保守派,长期把票投给左翼。他与中国籍朝鲜族的吴雄根结为友人,共同起诉日本政府,质问既然当年把吴雄根征用为“日本国民”的兵,如今为何又以“外国人”为由剥夺其获得补偿的资格?[7]
谦二有着一种难得的“他者想象力”:回忆西伯利亚时,他没有将苏联看守妖魔化,而是说他们同样是被战争与贫困压迫的普通人,这份克制与换位,是他一生的底色。正是这种跨越国族的姿态,使得谦二的反思不局限于日本社会内部,也指向战后世界更广阔的战争记忆结构。他的“精神返迁”并非忏悔式的陈词,而是将战争中的痛苦转化为同理心、责任感与行动力,把“回到日本”升华为“回到人的共同体”。
刘岩与谦二的行动撬动了战后制度与公共记忆的缝隙,构成了“精神返迁”的具体体现。所谓“精神返迁”,并非随身体回国便能达成,而是指个体在历史废墟中重新审视自身的位置,承认曾经的参与、选择与责任,并转向对他者的照护与历史记忆的重建。刘岩通过接生,洗净过去的耻感;谦二通过证言,拆解结构性暴力。他们都在长期持续的实践中挣脱了战后日本社会试图清除帝国历史责任的认同框架,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回家”。这正是他们主动选择“成为人”的结果。相比之下,那些虽已归国却仍沉溺于“哀史叙事”、拒绝反思殖民加害经验的人,依然未能走出帝国的幽影。
四、“此心安处是吾乡”: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对许多人而言,“回家”不仅仅是地理归返,更是生存的希望。奥斯威辛集中营在1944年圣诞节至1945年圣诞节这一年,死亡率是最高的。奥地利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尔对此指出,死亡高峰源于囚犯们相信圣诞前能回家。当这个希望破灭时,失落击垮了他们的心理防线,无数生命在绝望中悄然熄灭。[8]“回家”的信念成为极端暴力中维系自我的支点,寄托着爱、庇护与温暖的渴望。
正因如此,即便是在战场最残酷的“玉碎”时刻,士兵们喊出的仍是“妈妈——”这一呼喊,说明人在最极限的时刻依然本能地回到对亲情的依附。这种基本的人之情感,不分国籍,不依政体,是我们共同的人性起点。无论是核爆、轰炸、返迁还是占领,真正留下痕迹的,是普通人身上的痛与创。记住战争,不是为了胜败,而是为了“人”。[9]
然而,正是这份人性的疼痛与哀伤,在制度化的战后记忆中,被不断转译、消解,最终归于无声。返迁者常常选择沉默,但沉默的当事人与零散的史料,并不意味着历史本身的沉默。要理解返迁者的历史位置,需要重新审视他们在战争与战后秩序中所经历的“法西斯体制双重暴力”,即加害与受害交错的压迫。在战争时期,法西斯体制通过扩张、动员与殖民支配,将暴力施加于他者;而在帝国崩塌之后,它以“去殖民化”与“秩序重建”的名义,借由再分类、资格审查与身份净化等制度操作,反噬那些曾被动员的人。这种从显性的军事暴力到隐性的行政暴力的连续性,正是法西斯治理逻辑的变体延续。
面对这种逻辑对人的持续压迫,真正斩断其锁链不仅仅依赖审判、惩罚或宽恕等外部机制,更为艰难且同样关键的,是那些曾在结构性压迫中受益的群体,是否愿意主动承担责任、回应历史。这种责任意识不仅意味着回应他者的苦难,更包括跨界互证、正视多重真实,并参与防止历史重演的公共行动。这是从制度责任到道德主体自觉的转变,是从被动承受转向主动承担的过程。
而“反法西斯”的希望就在于,是否出现足够多的行动者愿意承担责任、回应历史,如刘岩与小熊谦二。他们的行动让“反战”不再停留于姿态,而是转化为持续可行的方法,让“赎罪”不只是象征性的口号,还要落地为具体的日常,让“回家”不仅是国家赋予的权利,也是一种面向他者的责任。他们的生命经验提醒我们:唯有成为真正的“人”,才能真正“回家”;唯有完成精神的返迁,才能抵达那片“有心上人等待着的白桦林”。
雪依然在下,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但心,终须找到一个真正的归属。
而此心安处,方为吾乡。
本文注释
[1][美]华乐瑞.当帝国回到家:战后日本的遣返与重整[M].黄煜文译.台北:远足文化,2018:41.
[2]详见毎日新闻社.在外邦人引扬の记录:この祖国への切なる慕情[M].东京:毎日新闻社,1970.厚生省援护局.引扬げと援护三十年の歩み[M].东京:厚生省,1977.引扬援护庁.引扬援护の记录[M].东京:クレス出版,2000.
[3][日]今井脩二.リラ咲く五月となれば.西原和海.満洲引揚げ文化人資料集·第2巻[D].金沢:金沢文圃閣,2016:182.
[4]大岛渚.儀式,1971.
[5]详见藤原てい.流れる星は生きている[M].東京:日比谷出版社,1949.
[6]蔺静.超越哀史与“人”之共情——重审战后日本返迁文学的研究方法[J].文艺争鸣,2021(8):158.
[7][日]小熊英二.活着回来的男人:一个普通日本兵的二战及战后生命史[M].黄耀进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314-316.
[8][奥]维克多·弗兰克尔.活出生命的意义[M].吕娜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23:91.
[9]王升远.“跨战争”视野与“战败体验”的文学史、思想史意义[J].山东社会科学,2020(6):92-93.
[本文为2024年度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一般项目“战后日本返迁叙事中的集体记忆与身份认同研究”(TJYY24-009)的阶段性成果。]
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25年09期“抗战专题”栏目。本文系未编排稿,成稿请查阅本刊。
来源 | 中国图书评论